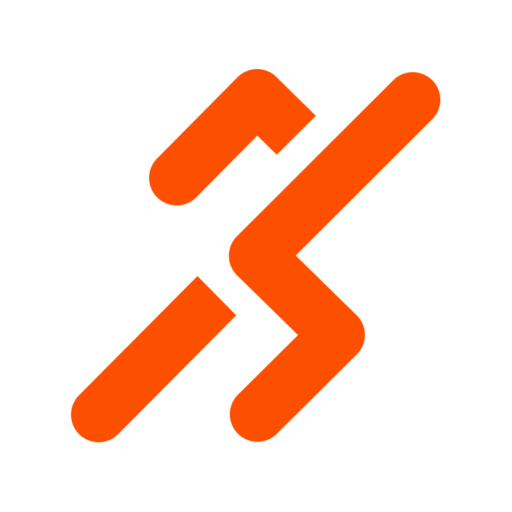写在前面的话
一年一度的Barkley Marathons又落下了帷幕,和去年只有两人完成Fun Run且无人最终完赛的平淡结果相比,无论是Jared Campbell最终成为了Barkley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三次完赛选手, Gary Robbins与幻觉苦苦搏斗直至止步在距终点仅十英里之地,还是John Kelly在第四圈关门前一刻钟才拖着疲惫透支的身体到达,又分秒不停决然悲壮地出发那注定不可能被完成的最后一圈,今年的这场赛事无疑更值得人们回味。从1988年起被沿用至今的著名标语“The Race That Eats Its Young”今年被换成了“Where Dreams Come to Die”,乍看绝望挫败之感溢于言表,可细细体会却也不尽然。
今年唯一的完赛者Jared Campbell一到达终点就被各路媒体和此起彼伏的闪光灯重重包围,而1988年,当Barkley历史上的第一位完赛者Edwin Furtaw冲过终点线时,等在那里的只有Carl的老婆Cathy和她的两个孩子。组织者Gary和Karl开车去补给站取包裹去了,其他人都回家了,Edwin摁停了自己的计时表,在那里边休息边等待Gary。周日下午的Frozen Head省立公园里悄无声息,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安静且平常,然而在时隔二十八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看见那个时刻所闪烁出的微光。接下来将要被讲述的这个故事,或许也是如此。
问道于盲

“可能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天黑了”她有些担心,而此时我正不耐烦地在河岸边搜寻着那两块石头,那里应该藏着我们要找的书。”
同往常一样,今年的赛道说明表述模糊令人困惑。当要找“溪流交汇处”的时候,我眼前有无数个这样的交汇处, “旁边有一排空心树”,眼前是成百棵那样的树,“和一堆石头”,成千的石头堆……依照我们此刻所选择的这条线路,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到达那个正确的峡谷,而此时我身旁的选手已经越来越冷,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为黑夜的即将来临而担惊受怕。那种担心迷失在丛林里的可怕的不确定感,会让最强悍的丛林好手也觉得备受折磨,更不要说对一个失去了视力的人。
我又找不到书了,我又得劝Rhonda原路返回,在这片已经露出丑恶嘴脸的森林里,我又看到了她对迷路的恐惧。
只是因为对这不可能着了迷
当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完全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可我是如此急切地想知道。

“梦想破灭的地方”- Barkley赛事总监Lazarus Lake
这是Laz(总监Gary Cantrell的化名)的Barkley新标语,他似乎挺引以为荣,他确实也该以此为荣。
无数世界顶级的超马选手都曾挑战Barkley而铩羽而归,大部分人是因为找不到书,严重偏离赛道,睡眠缺失到癫狂,或者以上皆有,而这些失误在这里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Barkley,之前有丰富的比赛经验显得毫无意义,无论你是完成过一个或者五百个超马赛其实都没什么区别,Barkley的考验要来得强烈得多,也深远得多,它根本就是为鞭笞你的精神和情感而诞生的。
Barkley历史上那些表现最好的选手们都有很好的地面导航和定位技能,事先在Frozen Head公园训练了足够多的时间,对这片森林、地貌和周边环境都已足够熟悉,而且通常已曾在此牛刀初试。如不具备以上条件,你在此地将希望渺茫。
其实即使具备以上所有条件你也希望渺茫。
由于大部分赛道是偏离既定山道的,一路上你得披荆斩棘,穿过锋利的枝杈,被藤蔓和落叶掩盖的裂缝,以及横倒的大树和烂树根,还要在陡峭山坡上艰难前行,导航能力此时就变得十分重要。只要迈错一步,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下到了一个错误的山谷,或者站上了一个错误的山头……甚至莫名其妙地到了一个不知是哪的镇上。

赛道上的选手,©John Price
盲人导航笔记
想想我必须辨认地上的每块石头,每条树根,每根枝杈,每个洞穴,每处拱起,以及所有非同寻常的障碍物,而在Barkley,所有的非同寻常都将成为寻常。
Rhonda跟我解释说她已经具备通过倾听向导的脚步声而判断方向的能力,所以她能清楚知道我在她的前方大概多远,一旦当我离她太远,她就可以提醒我放慢脚步。她希望我说话的时候都冲着前方而不是后方,因为冲后方说话会让我的位置显得比实际上的要近。另一个好办法是用手杖敲击那些障碍物,和我的脚步声一样,这能告诉她何时需要避开、绕过或是弯腰侧身躲过那些前方障碍物。
于是,当我们最后整理号码和检录即将出发时,她漫不经心地说“嗯,我觉得待会儿肯定特有意思,我以前都没爬过山的。”
Oh shit.
比赛的头天晚上,我睡在吊床上,认真思索我即将要面对的一切-一方面,我觉得她勇气可嘉,这可能是超马历史上最为艰难完赛率最低的一场百英里赛,而她愿意尝试,竟然相信我不会把她带迷路,不会因为我的无知对她造成伤害或者把事情弄糟。
而另一方面,“她愿意尝试,竟然相信我不会把她带迷路,不会因为我的无知对她造成伤害或者把事情弄糟。”-天哪,我一定不能辜负这个女人……在这个成功机会微乎其微的地方。
我们希望渺茫。
然而,真的就是这样吗?
要想在这里完赛全部五圈,赔率是10亿比1,就我以往对赛道的了解,考虑到要避开所有路障所耽误的时间,即使在13小时20分之内(这是这里每圈的关门时间)完成一圈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可我们都不该想太多,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不受伤不迷路不让自己死掉(你以前还在别的比赛里听过这种话吗?),向其他残障人士证明无论是在运动生涯还是日常生活里,你都可以无所不往,现在Rhonda就是那个高举火炬的人,这真是太TMD的酷了。
最艰巨的精神挑战
而这次的挑战跟身体无关。作为Rhonda的向导参与Barkley的一个好处可能在于,由于要一直维持很慢的跑速确保Rhonda跟得上,在我们30个小时的丛林历险中,95%的时间里我的身体感觉都很好,因为整个过程里我根本也没机会把自己推到极限。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精神上的。

对于那些不可言说的解释
在Barkley,首要原则就是你不能谈论Barkley,但我还是会尽我所能地呈现出我们在这里的经历,事实上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若非亲身经历,我想也没人能只通过文字就让我明白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况。但我们还是开始吧。
首先,我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件事:
1. 6页的Barkley赛道说明(其表述方式特别到要求极其细致的阅读理解)
2. 比赛头天晚上我们自己手绘的地图,然而也不一定100%正确。
3. 要确保Rhonda不绊倒不摔跤不被击中脸部不撞树不死掉。
然后,就像往常参加长距离比赛所需要注意的那样,注意保持体内水分、营养和电解质的平衡,不过相对于前面最重要的那三点,这些其实都再简单不过。
举例说明:
如果是我一个人跑,当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迷路时,我会在周边四处探寻以确定位置或者获得线索,并可以很迅速高效地完成这一切。譬如,如果要找一棵有树洞的树,我可以在五分钟之内就查看完前后四分之一英里范围内的两百棵树。但作为Rhonda的向导,我就不得不迁就她的速度,并且在查看树的同时,还要保证她不会撞向其中的某一棵。
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导航失误、反复的赛道查看和来回往返,都会花费比独自参赛要多得多的时间。另外,作为一个独立选手,一些小错误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因为你知道它们能被轻而易举地纠正,然而作为一个盲人选手的向导,情况就全然不是如此,从错误中返回所需的漫长时间将使人深感沮丧。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必须在重压下仍然保持积极乐观,因为我是向导——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向导,作为向导我还需要表现出激励自信的引导能力——一旦我的精神或者情绪开始崩溃,那我们就将必败无疑。
因此,在这样一场原本就被设计成想让选手们大错特错的比赛里,我居然疯狂地希望犯的错越少越好,而这一切所导致的戏剧性结果就是,我是如此强烈地想要不犯错,强烈到甚至会自己欺骗自己,带着主观意愿去阅读路线指南,更糟的是,我甚至有时会无视指南针的指向,觉得它肯定出了问题,因为“就是应该这么走。”
然而,大多数真实情况是,指南针完好无损,错的是我,你能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吗?
我一边导航,一边引导Rhonda前行,而大多数时候,所有这些都是在黑夜里完成的——偏离既定山道,披荆斩棘,冷得半死,而且通常我根本也不清楚我们到底是在山林里的哪个位置。
这是我迄今为止所做过的最激烈,最耗竭和最具挑战的事,一切仿佛都没有尽头,事情永远也不会变得容易那么一丁点。事实上,一旦你开始松懈,处境就会更艰难,更令人沮丧和绝望,而我之所以始终保持了积极态度,是因为我身在其中是为了Rhonda,而不是为了我自己。

特艰辛吧?
我的意思是,即使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仍然能想象得到那30个小时对我有多艰辛,是吗?
但是请不要忘了,我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是拥有着健全视力的。
而Rhonda只有8%的正常人视力。
她全部能做的就是遵循我的脚步并期待最好的结果,请试着想想单就这一点就需要何等的勇气。或许你可以在凌晨两点半拉上一位朋友去到你可以到达的最崎岖的山道上,在寒风里偏离山道走上1/4英里直到荒野的最深处,然后站在山谷的中央,闭上眼睛,往山顶的方向爬上几千尺,穿过所有的落叶、枝杈、荆棘和残骸,一路上只凭倾听你朋友的脚步声前进。
祝你好运吧。其实我敢打赌过不了一分钟你就会睁开眼睛。
而她却永远没机会睁开自己的眼睛。
最好的时光
我为我们在赛道上的表现自豪,除了我们俩没有人能真正明白:当我们最终得以穿越那片丛林回到终点时,我们是真的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们一直在走,总是来回反复,走错了很多路,在这片最崎岖的山地上,我们用双足行走了超过50英里。没有人能真正理解Rhonda和我究竟面临了怎样的挑战——然而,我们至始至终都心向光明,我们俩都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下表现了理解、勇气、谅解、无私和相互尊重。
我无法停止回忆,许许多多的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闪回:她攀爬在赛道最崎岖的路段上,低着头不说话,气喘吁吁,竭尽所能。她一步紧挨着一步,山道是那么陡峭,以至于任何一个停顿都会使得她有些往后踉跄,她只能用手杖来保持身体稳定,然后继续往前;我们用黑黢黢的手和膝盖在地上艰难地挪动,想要绕过“那些墙”去,结果后来往往发现眼前的坡度其实更陡,而此时都已精疲力竭。她一直在战斗,从未放弃,即使她想要放弃的时候,即使她说她已经受够了的时候。而当我们真想要退赛时,我们迷路了。
我们当时选了一条退出赛道返回起点的公路,结果发现走错了。我们迷路了,除了原路返回别无他法。我们会回到赛道上吗?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谁知道呢?也只有在Barkley你才会因为找退赛的路而迷路,而你决定继续比赛仅仅是因为你也找不出其他回到终点的好法子了。
直到看见直升机我们混乱的脑子才开始逐渐清晰,我先是试图说服她,接着又试图说服自己,那些直升机是来搜救我们的。当时我们已经在第一圈的赛道上待了26个小时,估计营地里所有的人都要急疯了,可事实是,除了我们,当时还有另外三名选手也处在同样的境况里——当然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切。
所以没错,那些直升机根本不是来找我们的。
这到底有没有可能?
Rhonda和我曾经讨论这件事到底能否做得到。她相信如果有两名向导——一个负责引路,一个负责导航——会让一切变得相对容易些,对此我很赞同,不过看来Laz并不会允许这种方案。
按规定完成赛道上的每一圈(必须在13小时20分钟之内完成)其实就让人难以置信,因为那意味着平均得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到一本书。大部分的赛段都不适合一个盲人选手跑,甚至快速移动都不太可能。“要想在Barkley准时完成每一圈你必须要跑一些赛段”,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你还得在找书过程中不犯任何一个错误。谁也没法打破这个定律,即使是那些最有经验的Barkley老鸟们。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做出了第一次尝试。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不可能之地的门,从那里出发,谁知道一个残障人士在Barkley能走到哪一步?
只有一个人知道。

这是一份礼物,是在我所有过往经历中所收获的最为独特最好的礼物。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Rhonda-Marie Avery所给予我的这个机会,我们友谊的种子因此萌芽,我已经等不及想在下一场赛事里当她的向导。第一次引导一位盲人跑者就在几乎最为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想之后其他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2016年的Barkley,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它,永远。

注:
Rhonda-Marie Avery, 加拿大安省越野跑运动员,2014年8月在20天之内跑完了885公里长的Bruce Trail,2015年10月以28小时40分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百英里赛Ghost Train Rail Trail Races,2016年4月,她成为了第一位挑战Barkley Marathons的残障人士。关于她的纪录片8% No Limit于2015年底在北美正式上映。
Christian Griffith,美国佐治亚州越野跑运动员,此前完成过多个百英里赛事,他将于今年7月参加美国密苏里州的Vol-State 500公里自补给赛。
感谢Christian Griffith将原文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授权翻译,以及他和Rhonda共同为我们讲述的Barkley故事,感谢一舟的校对和建议。
原创文章,作者:admin,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iranshao.com/25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