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為人,我很感激 -- Superrace 2016台灣站,之後。
我不會說因為這三天的經歷,使我對於人生有大澈大悟的體會,這樣未免過於矯情。但是多多少少,努力讓自己在賽道上保持清醒的過程中,對於「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我開始慢慢的可以抓住一點輪廓了。
所以在這裡,我不會太執著於介紹賽道的美,我想說的是,不管幾年以後,當我重新再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會知道是在哪一個時刻,因為被某些事物感動,而稍稍的改變了我對於人生的看法。如果經歷了一些年,那因為現實而逐漸消磨的熱情,還可以在重新看這篇文章的時候,提醒我自己,要保持對這個世界,充滿著好奇與感激的心情。
----------------------------------------------------------------------------------------------------
Date: 2016/1/22~1/24
「我到底在這裡幹什麼!?」這是我這三天問自己最多的一句話,尤其是在賽程第二天下午四點多,我一個人走在九棚沙漠的時候。

出發前新聞一直不停的報導說這個週末會有幾十年最強的極地寒流。但當我星期四到墾丁參加賽前講習的時候,當地氣溫將近30度,我實在不怎麼相信氣象預報。不過當第一天賽事結束,晚上在營地,工作人員集合選手講第二天的天氣狀況時,臉上露出十分擔心的表情,讓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對於天氣過於輕忽了。結果第二天凌晨四點起床後,開始颳風下雨,我只能穿著長袖排汗衣,加上輕薄的兩件風雨衣,在五點天未明時,跟大夥一起出發。而第一天就受傷的膝蓋,讓我對於自己能不能再跑,也沒有把握。
一早出發後我試著跑一下,右膝外側髂經束痛到讓我屈膝都有問題,我只好停下來用走的。然而今天的賽事有64公里,以我平地快走一小時5~6公里,上坡大約剩下4公里,加上到補給站休息的時間,我知道我今天要在這樣的天氣下,走14個小時。這下好了,從早上五點走到晚上七點,這究竟是什麼概念?
花了五個小時,從出發地下南田村走了25公里到了第二個補給站,一間當地居民民房的屋簷下。沿路風雨不斷,氣溫很低(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當天的氣溫只有六度,而體感溫度因為風雨的關係,大約只剩下二、三度吧),我全身一直發抖,手掌跟手指頭因為穿著被雨水打溼的手套而發皺慘白。我把裝備從我肩膀上卸下來,想要從裡面拿出鋼杯來泡即溶咖啡喝。但是手發抖的太厲害,沒辦法好好地打開鋼杯蓋,只好先吃點小魚乾跟堅果補充能量。過了幾分鐘,顫抖一直停不下來,我問一旁的醫護人員說:「這樣正常嗎?」
「正常啊,你的衣服都已經濕掉了,你要就繼續動,不要讓自己失溫,不然就上救護車,今天棄賽。」
離終點還有39公里,我還要花將近9個小時完成。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說服自己放棄,然後就輕鬆了。我可以直接到第二天的營地小墾丁渡假中心休息,泡個香積飯或是泡麵來吃,不用繼續吃甜到不行的能量包當營養來源。也可以換上溫暖乾爽的衣服,搞不好還可以小小的作弊一下,去泡個三溫暖什麼的。
我跑步的時間才兩年多,不長,全馬半馬跟越野跑加一加有七、八場。這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我想也會是我一輩子最深刻的馬拉松,不是我第一次完成的全馬,也不是第一次大阪的海外馬,而是一次在大佳河濱公園的星光馬。下午五點開始的賽事,晚上八點多,跑到28公里後,也是因為膝蓋疼痛,我覺得自己撐不住了,有一個念頭告訴自己:「每年有很多的馬拉松賽事,但是身體只有一個。」於是我跟工作人員說我要棄賽。當我回到家裡,陪當時六個月大的女兒玩,看著女兒被我逗的咯咯笑的時候,我腦中想的卻只是:「如果現在我還堅持在賽道上,應該已經完成35公里了.....」「就算我用走的,現在應該剩下2公里......」女兒睡了以後,我看著她的臉,喃喃地說:「現在的我,應該是完賽後,可以很驕傲的跟妳說爹地沒有放棄。」
「但是我放棄了。」
我發誓我不要再嘗試一次那時候的悔恨。於是我把雨衣穿上,背起背包,一個醫護人員很好心地把我的水壺裝滿熱水,放在我左胸口的水袋上,說這樣會比較舒服。這種溫暖的感覺在當天的氣候下,是充滿感激的溫度(不過大概也只能撐兩公里,又因為氣溫的關係,變成冷水)。
Johnny Cash 跟Fiona Apple在我的耳邊唱著Simon & Garfunkel的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我正走在旭海公路上。2002年Johnny Cash已經70歲了,用那歷經滄桑的聲音說著:
“If you need a friend, I am sailing right behi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ease your mind. ”
Fiona Apple 像是無法張開自己羽翼的金翅雀一般,刻意不讓自己甜甜慵懶的聲音太突出,壓低自己的喉嚨低沈地與Johnny Cash 合音。強風從左邊的海面上夾雜著雨水跟浪花打在我的臉上,我把防水外套再拉緊一點,低著頭繼續往前走。海面上沒有任何航行的船隻,我身邊沒有任何人。
“I will ease your mind.” 然後隔年Johnny Cash就死了。
我沒有看到旭海草原風光明媚色彩鮮明的樣子,我只能低著頭,看著地上的白線,不去想還有多遠的路途,一步步走下去。偶爾會有其他參賽選手從我旁邊跑過,跟我說聲加油,然後消失在下一個轉角。救護車從我前方開過來,醫護人員問我要不要上車,我搖搖手說不要。都已經走到這裡了,要放棄的話,一早就應該放棄了。
我聽說過對於潛水人員,有一個稱為「no turning point」,就是說,一旦過了這個點,你的氧氣殘餘量將不夠你返回出發點,所以你只能繼續往前,並希望在氧氣用盡以前,找到一個可以讓自己呼吸的地方。我已經完成了一半以上的路途了,不要想讓我坐上救護車。你們錯過了我的「no turning point」了,我在心裡這麼對自己說,帶有一點點驕傲,並且露出了只有我自己知道,安慰的微笑。
-------------------------------------------------------------------------------------------------------

我在九棚沙漠的時候覺得我是全世界最孤單的人。
下午四點多,我踏進九棚沙漠區,沿著主辦單位在地上插著,用來指引方向的小紅旗往前走。九棚沙漠較靠海的那端佈滿了小石頭,而賽道就經過那一區。海上吹來的風這會兒除了夾雜雨水跟浪花以外,同時也吹起地上的沙,撲簌簌的打在我臉上。我抬起頭來確定小紅旗的位置方向後,拉緊雨衣外套,低著頭,在即將轉暗的天色下繼續走。
九棚沙漠近年來因為有飆沙活動的關係,許多遊客來到這裡。當然今天沒有,不會有任何人在這樣的天氣想要坐吉普車在沙上來個180度迴轉的。右邊沙丘上沒有任何吉普車的胎痕,不過他們留下的許多垃圾,卻毫不留情的在我行走的地方張牙舞爪地存在著。
漲潮了。潮水把我的腳跟前方的小紅旗一起淹沒,我找不到繼續往前的方向,只能直愣愣的站著,等潮水退掉的時候,希望小紅旗還在原來的地方。被潮水捲起來的各式各樣的塑膠瓶、碎玻璃、廣告單等等,在我的腳邊漂阿漂的。我不知道這些垃圾是從海上漂過來的或是會被浪帶到其他地方去,但是我知道每年很多海裡面的海龜或是海豚或是鯨魚的,會把這些東西誤認為是水母之類的食物吃下去。不過跟真正的水母差別在於,它們懷有純粹且絕對的惡意,而且可以存在幾千年。
然後這些海龜或是海豚或是鯨魚的,就這樣死去了。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我為什麼會在這裡呢?」我的雙腳腳踝以下仍然浸在漲潮的海水裡,鞋子襪子全濕透了。不過海水的溫度帶來了一些暖意,讓我稍微舒服些。我把被雨水打溼的眼鏡拿下來,用身上的衣服擦了擦。即使我現在找不到問題的答案,起碼我還是要知道下一步應該要往哪兒走。
海水稍稍退了,我看到遠方有一些紅色的小標示慢慢浮出來。我覺得它們好遠好遠,似乎我永遠走不到那裡。我的身體仍舊不斷發抖,我必須時時繃緊自己上半身的肌肉,儘量利用手臂大動作的前後擺動帶領我前進,並且維持溫度。眼鏡又被雨打溼了,我的耳朵只聽得到我的雨衣因為風吹而發出的啪嗒啪嗒的聲音,像是試圖從我手上掙脫的魚所擺動的尾鰭般急劇。我想聽聽我家人的聲音,他們現在應該已經到墾丁我幫他們準備的民宿了。我希望他們可以幫我加油,而且讓我知道我離他們不遠。我把我放在雨衣防水口袋內的手機拿出來,按了常用號碼的快速鍵。
結果手機收不到訊號。
我還是連續播了兩三通,並不是在等待著接通的那一個瞬間,而是知道我只要等得夠久,我可以聽到有人跟我說話。
「您的電話將轉接至語音信箱,嘟聲後請留言........」
「謝謝,我把妳的話當成鼓勵了。」我對我的手機這麼說著。
兩個多小時後,我在晚上七點時抵達了第二天的營站,工作人員幫我拉起了布條,一直喊著加油加油。我剛認識的一位從海峽對岸來的朋友已經在營地等我很久了,一看到我回來,趕緊幫我卸下裝備、按摩我的肩膀。我換上乾的衣服後,跟他一起在火爐邊燒水烤火取暖,等著我的晚餐。
他簡單的跟我說了他上一輩的家世,跟台灣有很深的關係。一樣是在1949年那個顛沛混亂的時代,有些人到了台灣,有些人留在那兒。「上次,也是我第一次到台灣來,是兩年前,因為我爸」他說:「他有些親戚在這兒。那時候他生了病,想說以後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見面了,於是我就帶他來。」
「最後總算是有了了他的心願」他說。
晚上九點多,我在風雨之中沈沈睡去。外頭下著的雨慢慢變小,不知道雲縫中是否依稀看得到月光?
----------------------------------------------------------------------------------------------------
我不跟我爸說話已經超過半年了。
其實就是因為一些觀念上的不合而起了爭執,然後我就沒有回過我爸家裡看過他。他去年從服務四十多年的教職退休,現在一個人住在我們從小成長的家裡。小孩子全部都去外地工作了,也沒時間經常回家。所以以前從來不進廚房的他,現在開始懂得上市場買東西,自己在家裡煮簡單的三餐。如果今天沒有約朋友,他可能就一個人待在家裡一整天。以前每隔兩三天我就會接到他的電話,可能只是單純地問我吃過飯沒,或是他看到一些好看的電影推薦我去看。但自從爭執後,我們就沒有聯絡了。雖然每當我看到新聞報說天氣轉變,或是老人家開車危險的話題,都想打電話給他說聲注意身體,但就是因為自己的臭脾氣,寧可忍著,等到我那個想法消失。
然後我可以裝沒事過一天,直到下次又因為某些事情,觸動我的神經。我其實很想他,但是我跟我自己說還有我弟我妹可以照顧他,少我一個沒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嗎?不論是對我,或是對於我爸。
「家人嘛!沒有什麼過不了的。」我那位大陸朋友對我這麼說。
---------------------------------------------------------------------------------------------------

最後一天有20公里,也就是說以我之前的速度,約莫四小時可以到終點。但前兩天累積的疲勞,反而讓我在開始起跑不久以後,身體出現前所未有的疲憊。肩膀的疼痛依舊,右膝的疼痛沒有舒緩,左膝我想是因為我刻意避開右膝施力的關係,負荷過重,也開始痛了起來。雖然有七個小時左右的睡眠時間,瞌睡的感覺仍就像是不斷下在我身上的小雨般,無聲的滲入我的意識當中。我仍舊盯著地上的白線,想辦法讓自己因為專住而能夠保持意識,只是視線還是越來越模糊。
我必須想個辦法保持自己清醒。於是我開始每跨出一步,開始在心中默默的數數。1,2,3,4......好像有點用,讓我試試看把它說出來好了。5,6,7,8......精神好像越來越好了。我的步距用快步走的話大約有80公分,所以每數到一千,表示我可以前進800公尺左右,數到兩萬五,就應該到達終點了。那就專心做這件事吧,風還是很強,天空仍舊下著雨,身體依然是不斷發抖,手機也還是沒有訊號。
結果數到三千多我就失去意識了。
我發現這件事情的時候,想說應該自己應該是睡著了。不過讓我訝異的是,我還是繼續走著。應該是只有幾秒鐘的光景,因為在我失去意識之前記得的路邊的景色,離我不過十幾公尺。我想到曾經聽說過的關於行軍睡著的事情,他們在百公里的行軍當中,沒日沒夜地走著,如果累了,就會拉著前面的同袍的衣服,或是搭著他們的肩膀,低著頭睡一下,不過腳步不會停下來,好像身體已經記住了這種感覺,就像拳擊場上的選手們,即使被打到失去意識,身體依然記得平時練習的動作,還可以不斷揮拳,甚至擊倒對手,或者被對手擊倒。然後在意識回覆的時候,希望自己仍然可以站在那個六公尺見方的舞台上,直到這一回合的三分鐘結束。
我仍然站著,仍然走著,只是離終點還有十多公里,我還有三個小時要面對。雨變小了,氣溫還是很低,剛才在補給站裝的熱水也變冷了。我拿出口袋的糖果吃了幾顆。在體力不支的時候,有個甜的東西放在嘴巴,可以給我一些繼續下去的動力。

快到船舤石之前有個很陡峭的下坡,我跨了兩步,眼淚就流下來了。下坡時身體要維持平衡花的力氣,要用膝蓋來撐住,但是每跨出一步,膝蓋所感到的疼痛,遠遠超出我的想像。下坡看不到盡頭,而遠方的海面上,船帆石在雨中孤零零的朝向它想要前往的方向,但是一步也動不了。這幾千年或是幾萬年的歲月當中,他是否就這樣希望自己在被風化以及侵蝕而消融之前,可以往希望的方向前進,不論要再花幾千幾萬年。就像薛西佛斯推著永遠到不了山巔的石頭般,只是有著更深切的悲傷。
我想起我爸在我小時候教我唱的歌,歌詞大致上是說有一個人拿著水桶往外面潑水,結果潑到我的皮鞋上,而路上經過的人都在笑。我大聲地唱出來,反正現在也沒有什麼路上的人,也只有我自己會笑我自己而已。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想起這首歌,其實自己也不知道,或許是在我爸教我這首歌的時候,它就像某種流質滲進我記憶的核心裡面,並固執的附著在那兒。等到我幾乎脆弱到記憶的核因為意識模糊而逐漸剝落的時候,剩下的,就是附著其上的,最根本的我的組成。那個時候我爸巍巍然的背影,對我來說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而現在我自己當爸爸了,我可以留下什麼,給我最愛的女兒?
當我看到走在我前方的一個選手,倒著走這段下坡的時候,我忍不住笑了出來,因為樣子實在很滑稽。我趕上前與他一起前進,剩下大約兩公里了,只要再二十多分鐘,我就可以完成這場賽事。我把身上的糖果分給他吃,跟他聊天說笑,時間應該可以過得很快吧。
我家人在終點等著我,我看到她們了。這三天,我總共花了近29個小時在這場賽事上,現在可以結束了。我本來以為我會抱著我老婆跟我女兒好好的哭一場,但當我抱著我女兒,看著她用因為天冷而掛著鼻涕的臉叫我一聲「爹地」,我開心的笑了。這就是我回到終點的目的。我也一直相信,我能夠跑得那麼遠,是因為我有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慢慢地,我想,自己說不定也可以留下一個驕傲的背影,給我的下一代。

晚上,在休息的民宿外,我撥了個電話給我爸。他接起來後,我跟他說:「老爸,我完賽了.......」
這一路上有太多幫助過我的人了,有些人出現在我身邊,有些沒有,有些更只存在於記憶裡。但就是因為曾經有他們出現在我的生命當中,才有現在這個我。
生而為人,我很感激。
-------------------------------------------------------------------------------------------------
下一個賽事,應該會在沙漠裡。
「你不覺得這輩子有機會在沙漠中跑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嗎?」我開始對自己這麼說。
本文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看法,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有不同见解,原创频道欢迎您来分享。来源:爱燃烧 — http://iranshao.com/diaries/193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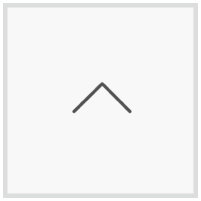

回应
回应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