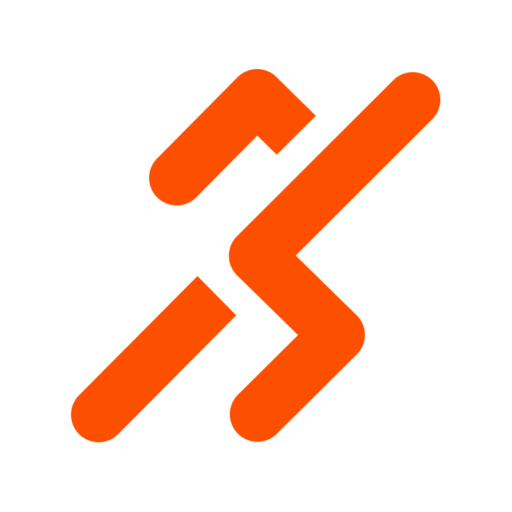我们刚进森林的时候,天还是全黑的。头天夜里突降暴雨,眼下林子里到处都湿漉漉的,动物们还躲在窝里没现身,连鸟儿都不出声了。在去起点的路上,我们紧紧跟着前面带路的车,中途还是差点错过了一个右拐的路口,险些一头栽进湖里去。此时四周漆黑一片,只有朦胧的迷雾在头灯的光影里悄无声息地蔓延,没有人察觉我们的到来,一切都非常隐秘而刺激。

original shot by Michael Li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麦船发消息问我要不要来跑这条环线,我几乎毫不迟疑地立马就答应了下来。安省北部Killarney省立公园里的这条La Cloche Silhouette步道全长73.1公里,分为Killarney Ridge(The Crack),Silver Peak,Hansen Township,Threenarrows和Baie Fine五区。这里一到秋天,树林里就会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地上铺满了红叶,走在上面简直就像踩在织锦上一般,若爬上连绵起伏的白石山登高远望,更是能一睹大自然恣意炫耀的风姿。可即使没有秋色,这条山径也颇为妙趣横生,直上直下的陡壁,巨石裂缝小溪瀑布,一路上几乎没有连通公路的出口,除了可以在有船道通行的Silver Peak中途撤离,没有其他的退路,大部分人都需要与世隔绝地花上一周时间才能走完整条环线。La Cloche是去往深处的长径,正是我朝思暮想想要跑的那种路。
此刻船长正一个人在前面雀跃,暗色里时不时传来他的嚎叫,后面也有人在短短长长地回应他,头天夜里大多数人几乎彻夜未眠,然而一出发人人都按捺不住地兴奋。眼下已是秋分时节,今年加东的天气却一反常态,入了秋气温反而节节拔高,高温天已经持续了两周,加上头天夜里的暴雨,此时森林里弥漫着浓重的湿气和树木腐烂的气息。水珠从树叶上一滴滴地滚落下来,脚下的树根又湿又滑,时不时地有人摔倒了,队伍却并没有因此而慢下来。
一年前船长就定下了此次行动的确切日期,尽管显得有些不管不顾,但这副绝不受任何人事耽搁的做派倒是让人觉得安心。三个月前他跟火娃花了三天时间背包徒步了整条线路,回来后出示了一份包括路线分析和完成时间的计划书,之后便销声匿迹杳无音信。一周前他突然现身,宣布由于停训了两个月,这回自己不跑全程只负责向导和后勤。自然引来一番苦劝,可大部分人还未来得及开口他就回心转意了,很明显他只是缺一粒定心丸而已。于是在这个黎明之前,由船长、我、火娃、久荣、杨磊和阿仁总共六人组成的小队潜入了森林的深处。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进入了Crack区的巨石阵和大裂缝,夜色渐渐淡了,雾却愈加浓厚。这条环线一路以钉在树上的蓝色标记引路,刚开始还算清楚,一进入巨石区,标记间距就明显拉长了,加上迷雾里能见度低,头灯的光散射得一塌糊涂,一时间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能靠近处依稀的石堆勉强辨别方向。

original shot by Michael Li

我对这一区记忆深刻。三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和胖胖一时兴起来Killarney看枫叶,几乎一口气走完了这里所有的短径,印象最深的还是Crack的这一段。巨石路段提不起来速,却让人心花怒放,我喜欢大石头堆出来的路,无论是美西的红岩,此地的白色石英石,还是雪山下的冰碛阵,爬啊钻啊挤啊跳啊的,我都爱得不得了,也许不过就是一种杂乱无章随心所欲的不管不顾。
来之前就晓得了那条著名的La Cloche长径。深秋的日照时间已经很短,落叶又会让路况变得更复杂,我什么功课都没做,根本就是一无所知,居然也郑重地考虑一个人把整条环道跑下来。那年我刚刚完成了第一场百英里,觉得自己简直无所不能,无论冒出什么想法马上付诸实现都是理所当然的,最终对夜里独自碰到黑熊的恐惧让我打了退堂鼓(当年我还从没在野外遇见过黑熊)。
辛苦的攀爬总会获得回报,从Crack的山顶放眼望去本该是浓墨重彩的山色水影,眼下四周却是雾霭溟濛,湖泊森林远山近树都沉没在雾海里,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可我们也兴奋得不得了,巨大的白石山如同悬浮在一片雾海中的孤岛,比起往常更显超凡脱俗之境,我们此刻便是身在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地方了。
—
船长带着其他人急匆匆地往前,我跟火娃在后头一路谈笑,渐渐拉开一小段距离。这条路船长走过十多回了,自然最有经验,路不好认,没有他带路,我们常常会犯糊涂,总要寻找辨认一番才能继续,这样一来反倒更慢了。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此番没有比赛的压力,没有成绩的追求,要是还不能说说笑笑嘻嘻哈哈那还有什么意思?
一路上船长总是念咒一样地告诫我们别太散漫,要抓紧白天的时间多跑点距离,我们当然不放在心上。可我们也摆脱不了他,他总像个山人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快跑呀,久荣他们往前头去了,他们已经跑出了节奏。跑出了节奏?脚下的路不是大滑石就是陡壁,或者两者兼是,这种路还能跑出什么节奏?一抬头,他又不见了。
雾终于散了,阳光立马就蹦出来,温度急剧地升起来了,可空气里还是很粘稠。也许是船长的苦口婆心终于见了效,火娃开始频频加速,顶着湿热一路狂奔。他坚决地说今天我们一定要追上船长,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必须要实现的目标。可前方不止有船长,还有他温柔的阿里山姑娘和胖胖,在我们出发后不久,他们也会带着食物从铃湖(Bell Lake)的渡口出发,划独木舟到Silver Peak泊船再徒步往前,他们会在前面设下我们一路上唯一的补给站,想要中途退出的人也可以随船离开,不过只有一个空位。

Nellie Lake (1933)—A.Y. Jackson
头一天我们去铃湖边订船,租船处的工作人员茫然地看了我们好久,才终于弄明白我们的计划并答应了我们提前租船的请求。随后他帮我们把船抬到渡口,以youtube教学视频的模式演示了划桨的姿势,并在教学中穿插了诸多自己以往英勇救援那些疯狂家伙的事迹,他反复强调等待救援的时候那些人的状态都特糟糕,糟透了简直像坨屎。
到补给站之前我们再次遇到了船长,意外的是其他人都还未出现。他们应该是在之前一个路口错过了左转,径直飞奔而去了,后来听说那是他们一路上跑得最潇洒的一段,果然是跑出了节奏。幸好他们及时回头了,于是在三分之一距离处所有成员再次会合了。见到火娃,阿里山姑娘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胖胖已经悠闲地吃了好一阵零食,我们只比预计晚到了两个小时,实在是出乎意料的顺利。
阿仁膝伤发作,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补给团的独木舟回去了,还剩下五个人继续前进。

original shot by Michael Li
—
告别阿里山姑娘后的火娃显得格外轻松,一路念叨着补给站的慰藉人心。午后太阳更炽烈了,我们奔跑在连绵起伏的白石山上,跟脚底下的石头一起被炎炎烈日烘烤。刚才修整的一会子,我吃了一根香蕉一个橘子一个鸡蛋一片面包外加半瓶可乐,看来胃口不错,说明今天的温度对我而言还算说得过去。
高温从来都是我的死敌,有次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喀斯喀特山区(Cascade Mountains)的一场比赛,恰巧碰到周边山火和干旱,才从起点出发据说体感温度就超过了38度。赛道一开始就是1500米的垂直海拔上升,我背了两升水上山,还没到12公里的第一个补给站就水库告罄了。一名男选手尾随我进了站,几乎在迈进水站的那一刹那他就一屁股坐到地上,抱着水桶大口猛灌起来,那时候进度已经很慢,看情形我估计他这回可能就到此为止了。然而我也没有运气好到哪里去,从一开始我就没吃下任何东西,等到晚上下了第二座山,心率已经高得离谱。我在那里退了赛,回到旅馆心率仍然很高,一夜无眠。第二天那里就降温了,还难得地下起了雨,我心里沮丧得无法自持,但也明白自己确实不可能撑过那个夜晚。
我的退赛纪录里十有八九都是因为高温,最惨的一次是有回在香港赶上了寒潮来前的湿热天,才刚爬完第一座山就全身滚烫连水都灌不下去,本来下午就决定退赛了,可我不甘心,都走到巴士站了又改主意返回去继续。
我期待的奇迹没有出现,很快就发现仅存的体力和精力也耗光了,我快要动不了,生平第一次感到呼吸困难,简直要活不成了。天已经黑了,那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蹦上去的台阶,每迈一步都要用尽全力。我数着数上台阶,每数五十下就要坐下来大口喘气,短短的几公里漫长得让人绝望。
好不容易终于下到山脚的村子里,赛道上的标记已经全没了,迷路,被村里的恶狗团团围住,黑漆漆空无一人的巷道以及门窗紧闭的万家灯火,那种感觉就仿佛自己成了一个游荡在人间之外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入口的幽灵,又好像是尘世恼怒于我毫无顾忌的背弃,一定要在我的重归路上设置重重障碍以增加磨难。最后,一只萍水相逢的黑猫给了我努力一搏的勇气,等到半夜终于折腾回旅馆房间时,我感觉自己真的奄奄一息了。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固然振奋人心,然而拼到弹尽粮绝实在十分凄惨。我们一离开香港寒潮就来了,温度陡降了将近三十度,如果……可就是没有如果。
—
一路上我们总遇到零星的徒步者,他们总问“你们也是18到24小时小组的成员吗?”18小时是火娃经过精密计算得到的结果,船长的目标是跑进24小时(也许他已经忘了自己之前说是12到18个小时)。我们和久荣杨磊前前后后地交替着前进,只有船长走得生风,总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后来他说其实是担心自己后劲不足拖累团队,决心拼出些前期速度来垫底。然而他担心的夜里后半程发力一直没有出现,于是在巨大的疑惑与不安中,他最终成了第一个走出山道的人。
刚才在半路上我们意外碰到了杨磊,他直挺挺地躺在大石头上,满脸的困倦,“我必须要睡一小会儿”,他答应我们不会停留超过半个小时,我们把公用的卫星电话塞进他背包里,又留了几粒咖啡因盐丸给他。他看起来一切都好,我和火娃仍然节奏悠闲,也许天黑前他就可以赶上我们。久荣因为害怕再次迷路,已经急忙往前去追船长了。
石头还是很滑,晒了半日的太阳,半干半湿的更可疑了,让人摸不准一脚踩上去的后果。从出发到现在我已经连着摔了好几跤,有好几次一只脚已经滑到半空,又靠着膝盖和大腿的力量强行反拉回来。也许顺其自然地摔倒反而好,可我还是克服不了内心的畏惧。
此刻我们应该是在第三区Hansen Township了,之前湿滑的石面后患无穷,不但让人畏畏缩缩不敢下脚,也无形中增加了许多肌肉和关节的劳损。跑了将近十个小时了,酸痛的膝盖,肿胀的脚掌,都一一显现,水泡们正在蓬勃生长,连下腹部也传来隐隐的闷痛,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

original shot by Michael Li
按照计划书,这条路如果按我们目前所选择的逆时针方向走该是绝对的先难后易,应该越跑越顺畅越跑越起飞,可眼下好多路段根本就是直上直下,一路上小溪也不少,要想安全地踩着石头过河,就得把重心压得极低,总之根本就是要时刻做好四驱的准备,攀岩屁降无所不用其极。

没有什么是无缘无故的。不到80公里的La Cloche不会无缘无故需要走上一个星期,一个根本没有海拔可言的州立公园环道赛不会无缘无故几十年坐稳最低完赛率的第一把交椅,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百英里赛道也不会无缘无故把关门时间放在48小时。可很多人似乎不大容易明白这个道理,我也不例外。
这路上的一切都像极了三个月前那场令人难忘的比赛。那条位于International Appalachian Trail上的赛道果然不同凡响,从一出发就一直让我惊奇,永无止尽的黑泥潭和乱石滩,一路跟随的飞蚊团和密密麻麻的肉虫珠帘,80公里之后我终于停止了自我欺骗,愈发艰难夸张的路况把最后一点微小的希望也彻底扑灭了,原来前面那些都只是热身而已。
在下又一座山的半山腰时,我在一段无休无止的暴石路上遇到了我的两个pacer,离开上个补给站时我离下站关门只剩不到6个小时(以这种地形路况完成该段28公里的可能性理论上为零),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竟然还肯相信我能按时通过。他们考虑了各种方案,第一个pacer已经把下一段的路线图看了又看,开心果壳吃了一车子,连补给包都帮我装好了,只等人一到就立马拽着冲向下一站。结果他们当然失望了,他们沮丧了,难过了,已经爆发的肾上腺素无处发泄了,于是干脆自己找上山来了。
重逢既开心又难过,既然没有了后顾之忧了,大家干脆以更慢的龟速继续。我的大腿肌肉已经崩溃了,我的脚趾甲统统要掉了,除了一脚密密麻麻的水泡,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从后面追上来的一名男选手一开口就大骂这比赛,在听说根本没有多少人通过前方关卡时又展露出了舒心的微笑。他急着赶回去报平安,我有两个pacer,大方地分给了他一个,他后来感激得不得了,手舞足蹈地为我的正式止步欢呼。我们所有人一起在被关门的地方合照,气氛并不伤感。
这实在是很狂野的一条赛道,还有山巅上那些瑟瑟的风响和林海的低吼,真是让人难忘的感觉啊,只是最后pacer们无路可跑终究让人遗憾,可事到如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那两位豁达的pacer也都明白这一点。

original shot by MPF
Runner和pacer之间的事情其实远不止付出与感谢那么简单。我曾经在安省北部的森林里见过一个焦躁不安的pacer,当时他正在百英里中途的营地旁来回踱步,冲每一个路过的人说“我的runner快来了,今年他训练特别好,待会我要是跟不上他那可怎么办?!”“进来!”他太太在房车里喊,他乖乖地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冲出来,朝着选手跑过来的方向紧张地张望。
其实pacer被runner拉爆也未必是多丢脸的事,有什么关系呢,这意味着有机会见证一场激动人心的运动表现。Jim Walmsley第一次去Western States就拉爆了发小James Bonnet(后者的WS最好成绩是第14名),他们一起才十公里就发现有些不对劲,Jim绝望地要后者不管使出什么法子无论如何都要跟上自己,可很快就放弃希望绝尘而去了。后来就像你们都知道的那样,Jim在离终点还有不到十迈的地方错过了一个左拐(那时候他还遥遥领先于赛事纪录),最后摄影车发现了躺在路边一动不动沮丧之极的他,终点前等待见证历史的人们心都碎了。
他还是慢慢走到了下一个补给站,他的pacer已经在那里等他很久了,他默默地和他一起再次出发,一直陪着他到了终点。当事后被问起此次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时,他pacer说要是午餐时没吃那个难吃的卷饼就好了。
温度已经不那么炽热了,Moose Pass上似乎吹起了隐隐的凉风,夕阳下有两只鹰在山与湖的上空盘旋。我和火娃在那里一声不响地站了很久,直到后面传来杖的敲击声,是杨磊赶上来与我们会合了。

La Cloche Panorama (1939)—Franklin Carmichael
未完待续
原创文章,作者:admin,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iranshao.com/41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