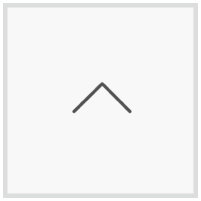《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如果你纯粹是被这本书的书名吸引过来的,翻开书时你或许会对它的内容大吃一惊,这时你怀着惊奇再合上书看一眼封面,会发现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从喀布尔到巴格达的战地报道》,其实这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作者戴斯特·费尔金斯(Dexter Filkins)目前是纽约客的作者,他曾作为《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南亚等地区驻扎了七八年的时间,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发回了许多重要的报道,并因此荣获了普利策奖。
那么这一切同跑步有什么关系呢?在翻开书本以前,我们或许会这样想象,在战争期间的喀布尔和巴格达,危险无处不在,人们或要“跑”着求生,“跑”着逃避死亡……其实没那么复杂,戴斯特只是在作为战地记者驻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期间,也照样保持了跑步的习惯而已。“只是”?或许我不该用这样的词……因为,你知道在战乱地区跑步会有多危险吗?
“晚上跑步,简直是疯了,我是在和死神调情,至少是自寻绑架。巴格达现在恢复到了自然状态,成了任何人都能为所欲为的地方。这里不再有法律,不再有法庭,什么都没有。……”
书中记录了作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期间的各种经历,他曾数度涉险,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目睹了很多死亡,他采访过基地组织成员,采访过伊拉克的“叛乱份子”,同海军陆战队队员朝夕相处,也同CIA和伊拉克政客打过交道。这些经历中,也包括他在当地跑步的经历。
他说当他跑步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孩子跟在他身后跑,有一次遇上一个叫法蒂玛的小女孩,路上遇到的伊拉克人说法蒂玛的亲人都死了,那天告别时她对戴斯特说了“明天见”,可他再也没有见过她……
伊拉克白天的气温高达50℃,所以他只能穿短裤跑,每天看着他跑步的伊拉克士兵有一次送了他一套伊拉克足球队的球衣,下身是长裤,于是他揣测可能是伊拉克士兵觉得他穿短裤跑步“有伤风化”。
在那些冲锋陷阵、人体炸弹、宗教冲突的故事之外,这些小小的故事时而透露着隐隐的悲伤,时而也透露着淡淡的人情味,它们似乎让人感觉到,在那些战火蔓延的地方,生活虽然残缺不全,但仍然在继续。
当然,作者并不是去为了感受这种“生活味”才会在这么危险的地方跑步,对于为什么要跑步,他如是阐述:
“我在伊拉克待了太久,已将近四年,我经历了一切——枪击、爆炸和死亡,但我从来都是安然无恙。我想我是麻木了,我感觉自己坚不可摧。危险于我而言只是一些概念,不完全是真实的,它们是我写的那些东西,杀死别人的那些东西。……现在,我已经不想那么多了,因为我总是能逃脱,我确实总是逃脱了。
唯一没有令我感到麻木的,是跑步。在底格里斯河岸上跑,和野狗一起跑,在这座垂死之城的黑暗之中跑,是我唯一能感觉到的东西。在巴格达这座最绝望的城市里,有那么短暂的幸福时刻,我能感觉我的心脏仍在跳动。”
看完整本书,重新套上为了方便携带而取下的书封时,看到了上面的导读:“即使在最绝望的城市,我们也要跑步,呼吸,生活,积极乐观地面对所发生的一切”,心里不禁有些嗤之以鼻。在战争期间的巴格达,“积极乐观”是可能的吗?
“在伊拉克时,我常感觉自己是在太空舱里,在最远的轨道上围着地球打转,好像斯普特尼克号里的莱卡——太空舱里的一条小狗。我不必再去计算时间,在失重状态下,给基地发回信号。家园是那么遥远,人们迫不及待地接收我的信息,他们无知而快乐,但迫切的程度令人动容。然后,我回去了,回到人群中间。回望那艘尚未返航的飞船,我感到自己似乎仍像莱卡一样,在正常的人群中飘浮。”
戴斯特写到一位叫拉尔夫·罗根(Ralph Logan)的下士,在回到美国后抢劫了一家汽车旅馆,但他没有带走钱,也没有逃跑,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自我惩罚。大部分活着离开战场的士兵仍然会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
“积极乐观”四个字并不是万能的,有时候,直面绝望反而更真诚坦荡些。
在找不到可以用来解释战争的“真理”的时候,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去念书本上出现过的每一个死者的姓名,和他们的家乡,即便我并无法完全记住。
2011年10月7日,第一届伊拉克国际马拉松在巴格达举办,共有1300名选手参加,其中1000名参加的是短程项目,全程和半程选手有300人。
伊拉克ICSSI组织的网站上这样写道:
我们为了使伊拉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跑。
我们奔跑,因为运动能促进友谊。
我们为自由而跑。
我们奔跑,为了伊拉克人能享受平等,享有同样的权力和责任。
我们奔跑,为了让巴格达再度成为一个和平的城市。
愿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