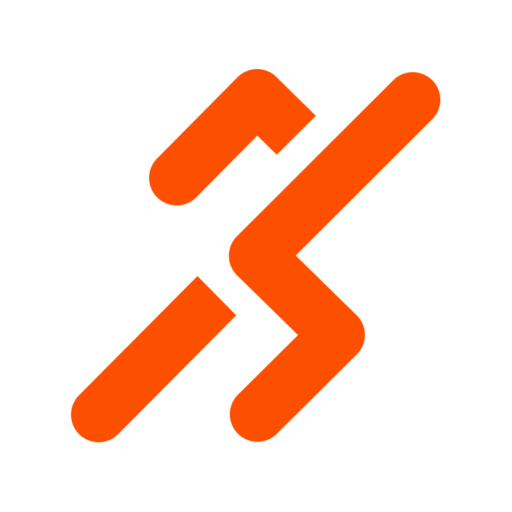围绕塞门亚的性别争议始终会继续。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如何支持和保护女性体育的发展,同时又能给予人类的边缘群体足够的尊重?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2014年,一名来自印度的高雄激素患者,杜蒂昌德(Dutee Chand)联合印度田径协会向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提交了仲裁申请。

杜蒂昌德(Dutee Chand)
她在14年英联邦运动会前被国家奥委会检查出患有高雄激素症,因而被取消了参赛资格(可能是考虑到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IAAF要求的正常标准),这个决定正缘于IAAF从2011年5月开始施行的关于女性运动员的参赛规定:患有高雄激素症的,法律意义上的女性不得参加女子组的比赛,除非她的雄激素水平在正常值以下。

左一,Santhi Soundarajan
昌德的申诉也得到了人权组织,包括本国的另一名著名运动员的支持,她就是桑蒂桑德拉扬(Santhi Soundarajan),作为中长跑运动员的她曾经为印度赢得过11枚国际比赛的奖牌。2006年亚洲运动会上,她在800米项目上获得一块银牌,但在随后的性别检测中,检测结果显示:“她没有女性的性别特征”,事实上她被检测出了Y染色体,但她的性征都呈现出女性的特点,显然,桑德拉扬是一名AIS(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患者。从此,桑德拉扬离开了赛道,那枚银牌也被剥夺了。
桑德拉扬在声援杜蒂时说:“他们在最后的关头对昌德进行了测试,侮辱了她,并让他伤心,这一切在新闻中都报道过了。现在,如果她重回赛场,事情并不会变得那么简单。她会遭到特别的对待,人们看待她的眼神都是怪异的。如果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更谨慎一些该多好。但是这件事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这样并不好。如果昌德是他们的女儿,人们又会怎么做呢?她的未来谁来负责?工作和收入是次要的问题,试想一下它将可能遭受到的。她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中,并非有权有势的又十分富裕。即使她能得到国家体育协会帮助,她还能在他的村子里安稳地生活下去吗?她会遇到结婚方面的困难。杜蒂并没有问题,而是体制有问题,一个运动员不能因为她的性别而输掉一切。”
当然,支持杜蒂的还有一些国际人权组织。

2015年6月,针对昌德的申诉,CAS做出了仲裁,决定在两年内,也就是到2017年7月为止,暂停IAAF制定的关于高雄激素症患者的女性参加田径比赛的规定,裁定的理由是:缺乏可以证明运动表现的提高与体内高雄激素水平存在关系的证据。因此,举证的任务就交给了IAAF,在这两年内IAAF如果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那么这条规定将被自动取消。

这样,昌德回到了赛场,也实现了她的奥运梦想。
敞开的大门
CAS的一纸裁决既为昌德敞开了大门,也为塞门亚这样的双性人提供了机会。至少从2015年7月以来,塞门亚似乎也受益匪浅,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训练与恢复的作用。(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其中的哪一个因素的作用更显著,两者是否存在协同作用?)
这扇大门的訇然中开,并非一蹴而就。
在1936年之前,一个叫Avery Brundage的人为了号召进行性别认证而举证了两位间性人:来自英国的Mary Louise Edith(后改名为Mark Weston)与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Zdeňka Koubková(后改名为Zdeněk Koubek),她们曾以女性的身份参加过国际比赛,在这之后都接受了变性手术,成为了男性。

二战后,国际奥委会(IOC,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规定了每个国家的奥委会都需要确认自己的女运动员真的是女性,当时采用的方式相当原始,就是脱光衣服进行观察,显然,很少有女运动员喜欢受到“裸体检阅”。
1966年,检阅被染色体测试取代了,任何不能通过这项测试的“女”运动员必须离开体育界。然而,在1985年的世界学生运动会的测试中,一名西班牙跨栏运动员却拒绝离开体坛。对此,一名西班牙医生向公众曝光了他是双性人的消息,她为此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她热爱的体育事业,她的赞助,还有尊严。

Maria Jose Martinez Patino
Maria其实和桑德拉扬一样,同样是一名AIS患者,“她”们虽然有Y染色体,虽然体内的雄激素水平很高,但由于她们的细胞无法对雄激素其反应,”她”们并不能因此占到便宜。至于AIS的患者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也多亏了Maria,虽然离开了体育界,她把目光转向了科研,她与Albert de La Chappelle 和 Arne Ljungqvist的合作,证明了AIS患者的以上特点。她把实现奥运梦想的机会给了更的人。
2009的塞门亚事件终于再次把双性人问题提上了议程:

2011年4月份,IAAF公布了《关于高雄激素患者参与女子项目比赛的管理规定》(IAAF Regulations Governing Eligibility of Females with Hyperandrogenism to Compete in Women’s Competition),提出了一个测定标准:要么证明自己患有AIS对雄性激素具有抗性,要么证明自己体内的睾酮水平低于10纳摩尔每毫升,否则就不能参加女子组的比赛。
不过,2015年的CAS的裁决似乎让历史开了倒车,那么,关于CAS裁定的理由,“缺乏可以证明运动表现的提高与体内高雄激素水平存在关系的证据”,真的合理吗?如果IAAF找不到支持的证据,这扇敞开的大门是否会让更多的高雄激素患者占据女子比赛的领奖台呢?
双性人为什么会受到限制?
古典的奥运会只允许男性参加,到了现代,女性在不断诉求着更平等的权利与地位,也在不断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可否认的是,女性能参加各类体育比赛是她们斗争的结果之一。

如果你还记得顾拜旦的《体育颂》,你一定会认同体育比赛无论从结果还是过程来看,都缺少不了公平公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男女分开进行比赛的缘故。如果男女运动员在一起比赛,女子绝无胜算。
当我们所在的时代越来接受(社会)性别的光谱化,然而我们的体育比赛仍然是依照二元对立的性别设置而展开,这并不是落后,也不是压抑。我们并非不接受双性人对自己属于女性的性别认同,否认她们的人权,而是无法接受可能存在着先天优势的双性人破坏女性比赛的公平性,无法接受她们可能对公平竞争原则的破坏。
然而,对于如何让双性人中认可自己女性身份的人参加女子比赛,我们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难题。IAAF之前所指定的测定睾酮水平的方法,虽然未必合理,也远非完美,但是这要好过没有任何限制。

乔安娜哈珀(Joanna Harper)
“首先我是一名科学家,其次我是一名运动员,最后我才是一个运动员,大部分科学家都支持IAAF的规则。”当被问到睾酮规则是否合理时,哈珀表明了立场。Joanna Harper今年58岁,他从2003年夏天开始进行激素治疗,在2005年春天被认可为女性,同时,她也是运动员和医学物理学家,她是促使国际奥委处理性别问题的团队中唯一一名变性人。
性别对于运动表现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一点和高个子打篮球有优势,拥有更多快肌的人短跑更有优势不同。我们的篮球比的不是高矮,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照顾长得矮的人;我们在短跑上比的不是肌肉的生化反应,神经反应,而是时间的快慢。所以,我们只考虑按照性别分组比赛。那么,为什么不设立一个第三性别组?我们可能为一个简单的决定而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问题:这样的做是包容,还是歧视?
参考:
2. IOC Consensus Meeting on Sex Reassignment and Hyperandrogenism3.Hyperandrogenism and women vs women vs men in sport: A Q&A with Joanna Harper
原创文章,作者:admin,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iranshao.com/2922.html